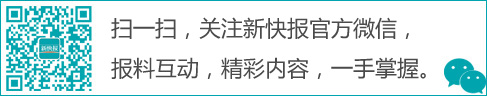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广州团队:防性侵教育的脚步走得越快 受害的孩子就会越少
■统筹:新快报记者 肖萍 采写: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近日,中国台湾女作家林奕含自杀了,她父母称其在未成年时遭老师性侵。一时间,人们纷纷猜测林奕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那个被补习班老师性侵而最终发疯的女孩就是她本人。但被指控的补习老师坚称两人曾为男女朋友关系并非性侵。
事件的真相尚未水落石出,却使得人们在为一个消逝的生命叹息的同时,将目光再次聚焦到保护儿童的问题上。
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预防。
为了尽可能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广州团队里有一群志愿者致力于将儿童防性侵公益讲座开进学校。一年下来,他们发现困难重重,“但也急不来,就一步一个脚印,点滴改变,柔软前行吧。”
防性侵和性教育是两个概念
目前,广州“女童保护”有三个团队,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男有女。其中,“大叔”陈晓涛牵头成立的“心暖花开”团队目前已经有140多名志愿者,11名志愿讲师,规模最大。
陈晓涛是队长,“头衔听起来挺大,其实我只是个卖鞋子的。”他自嘲道,对他而言,组建这样一个团队实属偶然。
有一天,10岁的女儿告诉陈晓涛,班上有一个特殊儿童,有时会在课堂上露出隐私部位。他突然意识到,女儿已经大了,应该掌握一些防性侵的知识。设立在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下的“女童保护”公益组织,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陈晓涛在网上联系了这个公益组织,希望他们能来学校为同学们上一节“爱护我们的身体”的防性侵课。通过这次联系,他才知道当时广州还没有比较成熟的团队,离得最近的讲师在韶关。
于是,陈晓涛决定要在广州组建一个团队,彼时,有着多年公益经验的他以为这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没想到学校拒绝他们来讲课,理由是担心引起孩子们对性的过多关注。虽然在陈晓涛的软磨硬泡下学校终于同意了,但提出了“三不要求”:不能拍照、不能拉横幅、不能派防性侵的宣传小册子。
完成了这节课后,陈晓涛一方面觉得很泄气,一方面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孩子们获取预防性侵害知识的途径太少了。
“首先他们可能混淆了概念,我们是做预防性侵的知识讲座,而不是性教育。性教育是系统的学科,需要这方面专业的老师。”陈晓涛说,授课的目的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隐私部位,爱护自己的身体,引导孩子们分辨和防范性侵害,并告诉孩子们,当遭遇性侵害的时候要怎么办,万一被侵害之后又如何应对等。
从游戏中学习防性侵知识
事实上,“防性侵教育”课堂的氛围并不像大人想象那样羞涩,反而更像是在做游戏。
讲师们以游戏的形式开始讲座,引导告诉孩子们身体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由一个“我说你指”的游戏引出隐私部位的概念——是小背心或是小内裤包裹的地方,并告诉孩子们,隐私部位不能随便让人看让人摸。通过助教演示以及互动帮助孩子们区分好的接触和不好的接触,让孩子们觉得不好的不舒服的奇怪的身体接触就属于性侵害了。接着,讲师就开始讲解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并教会孩子们遭遇性侵害时要分人多人少的场景应对性侵害,最后是告诉孩子们如果真的遭遇侵害要怎么办。每节课40分钟左右,“坏人是可以欺骗的”、“不要帮坏人保守秘密”、“遭遇性侵害不是孩子的错是坏人犯的错”等重要信息,讲师会细心告诉给每个听课孩子。
“学校、家长最担心的是我们教孩子们认识自己的隐私部位,从而引起过度关注,其实他们都知道的。”讲师之一的伍家泳说。她和蓝露璐来自于广州的另一个团队,两人都是广东工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也是目前广州女童保护授课最多的志愿讲师。
伍家泳已经讲了3次课,蓝露璐则讲了9次。“有一次我们和校长聊天问有没有小朋友反映曾经遭遇性侵,校长说孩子们有的说确实被人摸过隐私部位,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在被伤害。”这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还激动地说,“这个太可怕了,他们不知道被性侵又怎么能找信任的人说呢,结果只能一直忍着。”
被修改了52次的防性侵课件
陈晓涛特别强调,“女童保护”给孩子上防性侵课程的志愿讲师都要熟背课件,经过试讲,严格考核通过后,才能到一线讲课。他们有科学严谨的课件,要求讲师严格按照课件的内容讲述不能随意加多或删减。对此,刚刚成为志愿讲师的黎玮感触很深。她在第一次试讲中,因为给案例中的角色加入了具体名字而被扣分,最终只得了89分(满分100分,90分才算合格)而未通过考核。而后,她重新备课后再次试讲,最终以98分通过。陈晓涛解释道:“随意给案例主人公加名字容易造成联想。”
陈晓涛说,防性侵课件的内容都是在讲课实践中不断修正的,截止到目前已经修改了52次。
反复修改完善的目的是,确保不会引起孩子不适的同时教会孩子如何保护自己。比如,课件起初设定的是孩子遭遇性侵后应该第一时间告诉父母,但他们在讲课中发现,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并不在身边,怎么办?后来就改成了告诉信任的人。
“事后告诉谁,这一点很重要”,陈晓涛脸一沉,“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孩子告诉了同学的母亲她曾经被性侵,结果这位长辈却告诉自己的孩子‘以后别和她玩了,她很脏……’我想,当时那个女孩知道了这该是多么的崩溃。”
学校主动邀请团队去讲课
尽管困难重重,但一年下来,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着。
“有一次,我们在番禺一所学校讲完课不久,看到新闻报道,番禺有一个孩子成功逃脱了性侵。”蓝露璐说,“这不一定是我们的功劳,但总算是个好消息。”
有的家长希望他们能到自己孩子的学校讲课,只是在微信群上咨询意见时,因为有超过一半的家长不同意才作罢。不过,开始有学校主动邀请陈晓涛的团队去讲课,但这样的学校数量不多。
随着他们的志愿者队伍壮大,收到的个案多了起来。“心暖花开”团队管理成员之一郑晓霞最大的感触是:触目惊心。她加入女童保护团队后才知道,原来被性侵的不仅是女童还有男童,年龄跨度从几个月到十几岁都有。“那段时间我甚至不敢看群里面的消息,因为真的是很心疼那些被性侵的孩子,很想很想保护他们。对那些犯罪分子非常痛恨,但是一股很强烈的无力感笼罩着我。”
让人愤怒的个案很多,这些个案就像一把火,总能瞬间点燃志愿者的情绪,催促着他们快一点再快一点熟悉教案,去给孩子们上防性侵课。“防性侵教育的脚步走得越快,受害的孩子就会越少,能帮一个是一个。”讲师黎玮说道。
面对这些个案陈晓涛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无助。“作为防性侵教育的团队,我们事后能做的很少,但很多受害者的家人会向我们求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奈。有一位母亲告诉陈晓涛,自己4岁的女儿被邻居性侵了,要求他们陪着一起去录口供,但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不是专业人士,做得不好很容易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但这位母亲很坚持,他只能婉拒并介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帮忙,“可以预见,这个孩子的心理还是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种伤害究竟有多可怕?此前有媒体报道,在北京有一位女童保护的讲师曾经遭遇过性侵,从受害者到志愿者是非常艰难的跨越,如今已经走出阴霾。“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我们志愿团队中也有这样的人。最终她连课件都没法完全读完。”陈晓涛突然停顿下来,似乎经过很长的思考,“所以有些伤感你不可以想象,但也急不来,就一步一个脚印,点滴改变,柔软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