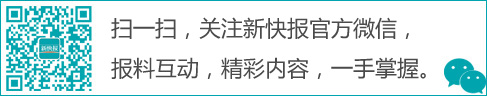







■姚涯屏
又要过年了。
到了我这个年纪,过年时更多的是感慨,感慨时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河流远去,再也不会回来。比如,十八岁的我。那年冬天,一个文艺青年,在沁入骨髓的寒风中,攥着一张简单的地图,坐了四趟长途短途公交车,从湘中前往邵阳地区,去寻找滩头镇。
去滩头镇,是因为年画。湖南最出名的年画在滩头。
年画是为信仰而生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神很多,有个词叫“满天神佛”。大门有门神神荼郁垒秦叔宝尉迟恭,堂屋神台有送子观音赵公元帅,厨房灶台有灶王爷。俗话说离地三尺有神灵,其实地上还有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果觉得神像表达愿望都不够直接,还可以印成万字不到头的纹样镶嵌吉语文字来祈求。厅房要“和气致祥”、“子孙万代”、“年年发财”、“金玉满堂”。仓库要“五谷丰登”,畜栏要“六畜兴旺”。祈求以外,还要喻教化于娱乐。所以房间还要有《老鼠娶亲》、《麒麟送子》、《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等戏文——鲁迅小时候房间里就贴过一张《老鼠娶亲》。有财力者当然可以直接叫人画。我曾临摹过恩师王憨山先生借回来的《土地公公像》,六七寸高的裱板小幅,精致典雅。作者据说是萧乡陔,教过齐白石画人物画的。但总的来说,请人画的成本很高,大多数人家只能请些木版年画回去贴。黝黑的门板上贴上年画,整个门脸就精神起来了。
说起年画,大家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当然是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的潍坊,就像说起青花瓷器大家都会想起景德镇。但广东大埔也有高陂青花瓷,湖南邵阳也有滩头年画。有人称滩头年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我估计其它“三大”不怎么乐意和它同坐一排。但滩头年画也不是等闲之辈。《老鼠娶亲》上有“楚南滩镇新刻老鼠娶亲全本”字样,明末滩头镇就叫楚南滩镇,据说称楚南而不称湖南,说明滩头年画确实历史悠久,至少追溯到明代;滩头年画曾销往两湖、两广、云贵、陕赣和东南亚等地,贵州商业部门一九七九年曾要求滩头生产年画供应贵州。贵州商业部门跑来湖南下订单,也说明其江湖地位。这么有江湖地位的年画,竟然窝在山沟里,这是与其它“三大”完全不同的地方。
窝在山沟里有窝在山沟里的好处,首先是它自成体系的生产流程。从造纸制料刻版到印刷开脸,都是在当地完成,不受外地材料供应的影响,甚至有些材料不是哪里都能找到,比如涂布在纸面的“白胶泥”。另外,滩头年画扎根乡土,甚至还有表现苗族英雄的作品,这也是它独特的地方。在审美上,它至少不像某些年画那样,受到了各种所谓雅文化的影响,成了粗简版的复制国画。滩头年画窝在山沟里,保持了它民间艺术的独立性,所以它更淳朴,淳朴得像雪峰山,淳朴得像湘西汉子。大面积平涂的黄丹、槐黄、藤黄、叶绿、靛青,压上大刀阔斧的黑,动人心魄。原籍湖南邵阳的临桂人况周颐先生在《蕙风词话》里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估计况先生小时候看到家里贴的滩头年画,就已经感受到“重、拙、大”了。况先生说的是词,其实艺术是相通的,回头看湖湘的艺术史,从欧阳询、怀素,到曾国藩、齐白石,“重、拙、大”是一以贯之的。恩师王憨山先生毕生的艺术实践,都在极力主张并践行“重、拙、大”的艺术追求。
所以我要去滩头,要去滩头朝圣。
从破了玻璃窗的公交车上哆哆嗦嗦地下来,到了滩头,并没有我想象中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和堆积如山的各式年画,冷清得像破车厢里那沁入骨髓的寒风。我见到了滩头年画的老行尊——高腊梅老太太。那时她五十七八,其实也不算老太太。老太太和她丈夫钟海仙先生带我参观了作坊。在我印象里,这个作坊也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居,嘎吱嘎吱作响的木阁楼上摆着印制年画的案台,案台右边安放着盛颜料的瓦缸,案台左边就是一块印版,厚实得不需要其它任何东西固定。光线斜照在黑漆漆的厚实印版上,隐隐散发着幽迷的光。印版的左边是另一张桌子,桌边夹着一叠没印完的年画。屋梁下横排着十来根竹竿,一叠叠年画半成品用更细的竹竿夹住,横晾在大竹竿上。墙角堆着各色印版,黑的红的黄的绿的,好看的同时,又旁溢出点湘楚文化的诡异。作坊里只有高腊梅两口子,而且似乎并没有在开工。老太太亲自印了给我看:她站在案前,右手竖抓着粗犷的棕帚,蘸了颜料,似乎还在颜料瓦缸里的一根小竹子上篦了一下,再刷匀在印版上,左手把纸覆过来,右手换另一个干净棕帚在背面擦刷,左手再把纸揭起来,垂入印版与纸夹的空隙中。然后再重复这个程序。
当时我买了几百张年画,捆成了一大捆。来之前听说还有一两家做年画的,可天色已晚,来不及去寻访,只能循原路回去。回去后碰上同好就送,就像信徒流通经书,就像年轻人肆意挥霍时间。恩师王憨山先生喜欢,我也呈上一整套。转眼二十八年了,那个十八岁的文艺青年变成了中年油腻男,感觉时钟越转越快。所藏的年画也像时间一样,送出一对少一对了。
后来,我再没去过滩头,只是偶尔听到一些关于滩头年画的故事:有关部门又下大力气去支持啦,学徒学了几天宁可去挖煤啦,高腊梅后人回家学艺啦,谁又呼吁抢救啦,电视台又去拍专题片啦……听上去似乎有好消息有坏消息,其实都是坏消息——一个健康成长的人是不需要大家反复去慰问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是不需要倾斜性支持的。二〇〇三年二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的新闻发布会上,滩头年画被列入该工程的首批项目。十五年过去了,不知道抢救成什么样子了。我也不是个泥古的遗老,深知凡是到了抢救的程度,就算抢救过来,没有合适的土壤,它也无非是吊着口气,奄奄一息,好死不如赖活着。二〇一四年冬天,高老太太八十一岁,去了另一个世界做她喜欢的年画。她的丈夫已经先她而去了。当时我写了《由过年想到滩头年画》,来纪念这位有过一面之缘的年画老行尊。随着一位位老艺人的离去,这些民间艺术会怎么样呢?现在又是冬天,又过年了,大喜的日子,来讲这些有点伤感的事情,无非是念着“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励志诗句,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春天,能有更多好庄稼生长在这片有滩头年画滋润过的土地上,能更加壮硕地成长起来。这才是像滩头年画这样的民间艺术曾经红红火火地存在过的重要意义。
■整理:潘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