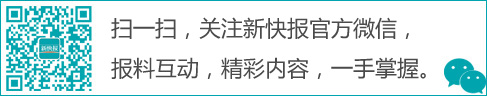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受访者:史国良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才》杂志就有一篇《史国良求师记》的文章,讲到我找黄胄先生的经过,美术界的人都说:“史国良是个幸运儿,事业一帆风顺。”其实那幸运的来源,正是因为我找到了好老师,走对了方向。
要讲到我和黄胄老师的缘分,就得从那盏灯说起,二十多年过去了,那盏灯一直亮在我心头,成了我艺术道路上的坐标。
当年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喜欢黄胄的画到了崇拜的程度,渴望拜他为师。但没人为我搭桥,也没人给我引荐,完全是一种力量的驱使, 我自己找上门来的。黄胄那时是久负盛名的大画家,想见到他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他能否答应我做学生则更不容易了。但是,“渴望”让我不顾一切,我扛上一卷画,上路了。
从发表的画作上看,只知黄胄在军事博物馆工作,我先到了军博。门卫告诉我,“黄胄已调离。”于是,我又转到军博宿舍,楼下的孩子告诉我 “黄胄搬家了,搬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下楼来的大人讲,黄胄搬到了三里河一带,不知具体地址。还向我介绍,黄胄很严厉,门上常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
失望之余,我又感到一线希望,因为已掌握了两个信息,一是“三里河一带”,二是门上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我骑上车子,奔向了三里河。从军博到三里河不算远,但到了三里河才傻了眼,四处都是一排排的楼群,哪一座才是黄胄的家呢?我决定挨楼地找,爬上爬下,见人就问, “黄胄住在这儿吗?”都是摇头,说不知道,再反问我,“他住几楼呀?”我也摇头说不知道。一位好心人说:“小伙子回去吧,连门牌号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你看天都黑了。”
是啊,从早找到晚,饿着肚子,也没找到黄胄的家,敲了多少个门,都没见到那张“谢绝来访”的纸条。失望极了。返回家的路上难过得只想哭,身上扛的那卷画真的千斤重似的,学画真难呀!
走到白石桥,我还是不甘心,指天发誓,再回去找一次,找到了,我和他有缘,找不到从此不再来,我调转自行车头,又一次返回了三里河。
找啊找,黄胄老师,您到底住在哪里呢?会不会那人记错了您的方向?会不会他在和我开玩笑?唉!找黄胄老师找得我好苦呀!
猛然,我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座楼顶上,亮着一盏灯,全楼都黑着,只有那窗口亮着那一盏,会不会就是那盏灯呢?在一片黑暗中,那盏灯多美呀,我开始热血沸腾,不顾一天的劳累,冲向了那盏灯。
五层楼并不高,往日几步就蹿上去了,可今天,脚上就如同灌了铅。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到了门口,竟没了勇气敲门,因为门上并没有纸条。此时此刻,心都碎了。闭着眼睛,愣了一会儿,终于,抬起我那被汗水洇湿了的手,敲了门。
门并没开,里面有一位女人在问:“你找谁?”“是黄胄家吗?”“你是谁?”甭问了,这正是黄胄家,我是谁?一个毛孩子,一个傻小子,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说:“我是他的学生。”
门开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站在我面前,一脸的疑问,看到我手里抱着一卷画,才让我进来,后来我知道,他就是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老师。
黄胄并不像别人说得那么严厉,只是严格,严格中带几分亲切,当他看过了我的画,不但笑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画得还不错,就做我的学生吧。”终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不但找到了那盏灯,而且,从此也走进了那盏灯。再后来的艺术道路上,像很多人讲的那样,“我成为了幸运儿”。
黄胄先生画新疆,他建议我画西藏,他说:“自己年轻时也去过西藏,但没能做更深入研究,但那个地方可画的东西很丰富,只要能深入进去,一定能画出好作品。”
于是我从原来画北方农村,转画了西藏。第一次去西藏,先生还把自己穿过的皮大衣送给了我,说那个地方冷,路上用得着。
这件大衣曾作过道具,在他画《高原子弟兵》中出现过。我是从青藏公路进藏的,先从西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搭长途汽车,坐上两天两夜到拉萨,中途还要翻越唐古拉山,多亏这件大衣,不然真冻坏了。每次媒体约我写有关先生的文章,都想让我找几张与先生合影的照片。似乎社会上已经有那么一条约定俗成的套路了,你是谁的学生必有合影作证明似的。每当面对这种要求时,我一是苦笑,二是尴尬, 因为虽与先生学画多年,竟没一张与先生单独的合影照。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真想与先生照张相,挂在自己家中或办公室里,有这个虚荣心,却没钱买相机。有次下乡,借了单位里的海鸥120相机,结果不会操作,一张相没照就让我给弄坏了,还赔了不少钱。那一次教训让我直至今日对机械操作的东西都敬而远之。不过也成就了我,每次下乡就拼命地画速写,还养成了用速写纪录生活的习惯。再后来,经常与先生在一起,帮他研墨,抻纸,经常看往来的宾客和先生合影,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人家帮我照张相,再寄给我。总觉得那样对先生不好,也显得没面子。
等我想到有必要与先生合影时,先生住进了医院,样子很不好看,而且很疲倦,看我一身僧服,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只当你说着玩呢,还动真格的了。”我摸着兜里的相机,几回想拿出来,总不忍心,改日吧!于是我失去了最后一次与先生合影的机会。每当看到别的学生画册里印着与先生合影照片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嫉妒、羡慕、遗憾,反正挺复杂的。
我和黄胄先生的缘分,多亏了五楼顶层的那盏灯,那灯光伴我走过了太行山、黄土高坡,走上了青藏高原又走到了大洋彼岸。那盏灯带给了我信心,也送来了温暖,让我忘不了黄胄先生,也忘不了那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