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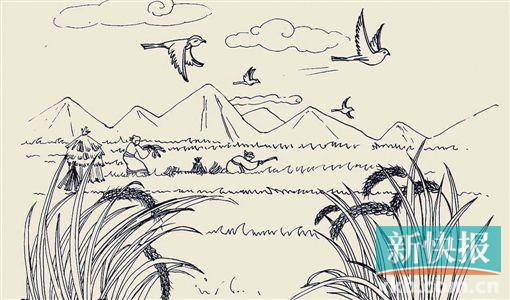



广州南越文王墓后藏室是一个储放炊煮、烧烤厨具和大小容器及珍馐食品的库房,面积还不到4平方米。室内层层堆叠着上百件大型炊具与容器,其中铜炊器有鼎18件。其中一个铁鼎的造型与广州华侨新村等处南越墓群出土的越式陶鼎类同,由此肯定是当地所铸。说明南越国时期本地已能生产如此大型的铸铁器件,这比之过去一直认为广州直到晋代始“大开鼓铸”的记载要提前五百年。
南越国时期广州已能生产大型的铸铁器件
后藏室是一个储放炊煮、烧烤厨具和大小容器及珍馐食品的库房。后藏室仅长2米、宽1.8米,面积还不到4平方米。室内层层堆叠着上百件大型炊具与容器,其中铜炊器有鼎18件,分汉式(即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器型)和越式两种,最大的两件是越式鼎,身如锅形,平底、竖耳,三扁足微外撇,高55厘米、口径51.7厘米,侧置室中,有1件被断落的一块挑檐大石打中,腹部裂开一个口子,微凹陷,此鼎被2米高处重五六百斤的大石砸下,没被砸扁,也没全碎,足见铜胎的坚硬。另有大铜烤炉两件,煎炉1件,釜1对,大小铜鍪10余件,都带铁三足架,以及蒜头壶、洗、鋗、匜、灯、提筒等56件铜器。室门口的1个大铁鼎,敛口、直唇、身呈釜形,肩处有两个耳,蹄形直足,高48厘米,重26.2公斤。这个铁鼎的造型与广州华侨新村等处南越墓群出土的越式陶鼎类同,由此肯定是当地所铸。说明南越国时期本地已能生产如此大型的铸铁器件,这比之过去一直认为广州直到晋代始“大开鼓铸”的记载要提前五百年。
在后藏室的陶器、铜炊器和容器中,有30多件器内存有动物遗骸,还有果品等残留,其中以水产品最多,禽畜类次之。另外,在东耳室和东侧室,在陶的或铜的容器内,也发现一些海产品和禽畜的遗骸,应是作为食品随葬。但西侧室最特殊,出土的动物遗骸,是直接放在地板上,有的还与殉人的骨骼相混,部分还有烧烤痕迹,主要是猪、牛、羊,应属祭奠的牺牲。
出土动物遗骸中禾花雀颇引人注意
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动物遗骸,数量多,种类丰富,在全国的汉墓中是不多见的,有家猪、黄牛、山羊、家鸡、鲤、大黄鱼、广东鲂、河蚬、虾、中华花龟、中华鳖、青蚶(2000多个体)、龟足(1500多个体)、楔形斧蛤(200多个体)、耳螺、笋壳螺、禾花雀(200多个体)和竹鼠。这些动物在广东地区都有现生种,没有发现有非本地区产的动物,具有鲜明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动物区系的特点。比如鲤科鱼类和龟鳖类都是典型淡水生物;耳螺、笋壳螺和河蚬等软体动物,属淡水与半咸水生物,主要栖息于珠江三角洲的河口地区,青蚶、楔形斧蛤、龟足等是我国南方沿海常见的种类。
在这批出土动物遗骸中,以禾花雀颇引人注意,直到今天仍被本地区居民视为佳肴(编者注:禾花雀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未列为濒危保护动物),说明该物种的习性、迁徙路线似乎两千年来无大的变化。禾花雀是候鸟,每年冬至前后,从东北飞到福建、广东一带,啄食灌浆的稻谷。当时居处岭南的越人大概已掌握了禾花雀怕人、怕光、怕影和白天采食稻谷黄昏栖于禾田的习性。人们要张网捕捉,动作需敏捷,无声作业,配合默契,才能一网尽收。墓内有如此大量的个体遗骸,说明当时广州附近的农业耕作已是稻田连片了。禾花雀出于后藏室的三个陶罐之中,出土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异的现象,即有不少黏土陶粒和炭粒混同一起。估计这是当时一种焗烤的食法,即小雀去毛之后,放在一个陶容器中,把烧红的陶土粒与炭粒堆盖其上,借助这样的高温把雀体烤熟而食;今天广东的东江名菜盐焗鸡就是借助炒得炽热的粗盐粒把鸡烫熟的。同时,在这些禾花雀骨骼中,不见有头骨、跗趾骨和脚爪,这也和今天广东人去其头足的食用习惯相同。
两千年前的广州(番禺)处于珠江河口的位置,其地形地貌总的来讲是地势低平、河汊纵横、水网密布、岩礁林立、海岸曲折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夏长冬暖,雨量充沛。象岗汉墓中出土的青蚶、龟足、楔形斧蛤等海产动物特多,但在今天广州市区的珠江河汊上几乎绝迹了,要到现今的珠江出海口,即广州东面约20公里的黄埔区以外甚至到惠阳沿海地区才见有分布。说明经历两千年的沧桑变化,珠江出海口已外延有20公里了。古代交通欠发达,又没有保鲜技术条件的保证,这些海产只可能是就近捕捞而得,而不会从远处运来。
(本文据西汉南越王墓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