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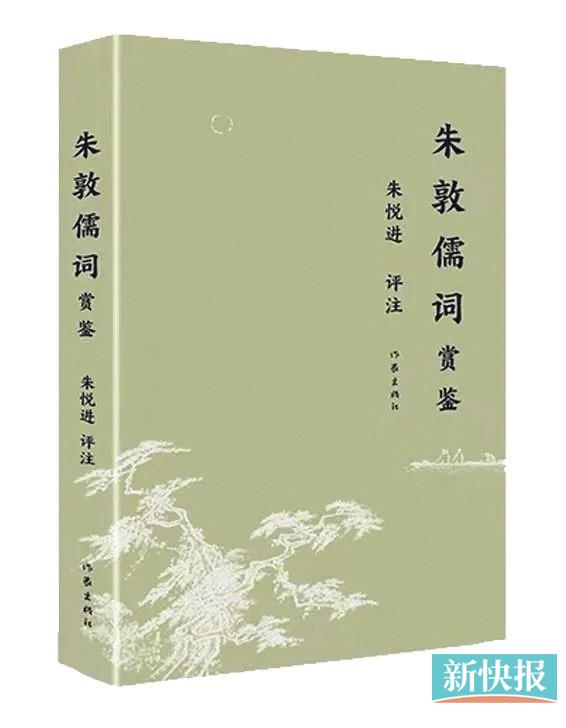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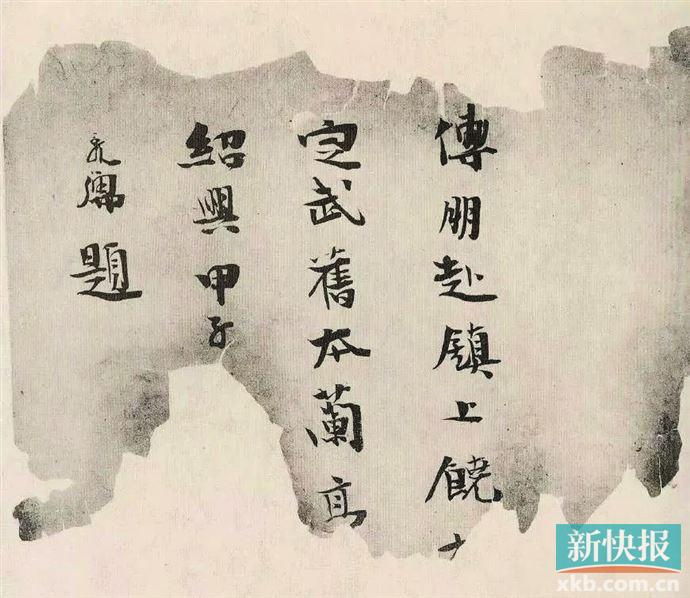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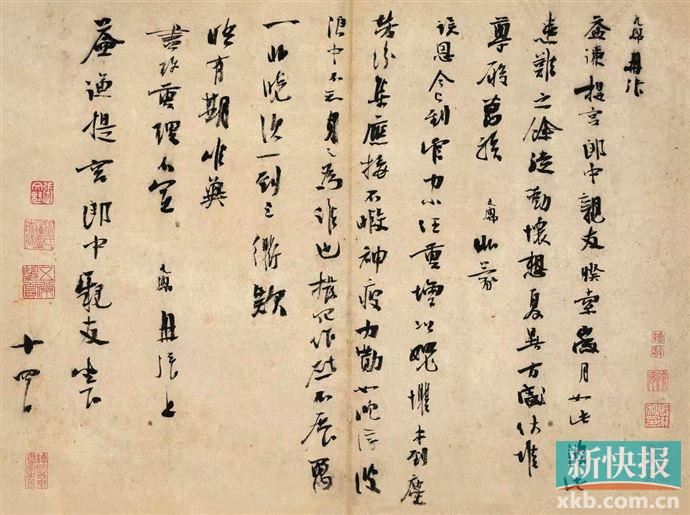
朱敦儒后裔、资深新闻人朱悦进(笔名阅尽)新书《朱敦儒词赏鉴》日前出版
近日,朱悦进的新书《朱敦儒词赏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朱敦儒是两宋之交的文学巨擘,对宋词词风转变贡献至伟。朱敦儒后裔、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朱悦进先生,从事新闻工作近四十年,曾任《粤港信息日报》副总编辑,近年致力于朱敦儒词章的研究与诠释。日前,他就朱敦儒的词史地位等话题,接受了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的专访。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收藏周刊:请您介绍一下关于朱敦儒先生词章的研究和著述缘起。
朱悦进:唐诗宋词在我国有着广泛读者基础。喜爱唐诗宋词,更是大学中文系学子的共同特征。我母校陕西师大的中文系又很著名,自己对唐诗宋词的喜爱自然又多几分。记得大学时,每天清晨,背诵唐诗宋词是“必修课”。
但说起对朱敦儒词的研究,却比较晚。我少小离乡,在外生活工作几十年,对故乡及家族渊源所知甚少。临退休前,有次回乡,偶然看到家谱,方知朱敦儒是自己先祖。这才开始关注、搜集朱敦儒词和相关书籍。随着阅读深入,我对朱敦儒词的文学价值及对词史的贡献也越钦佩,这也越激发起自己研究朱词的兴趣。
其间,我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朱敦儒词在现代的影响力远不及他所处时代,包括大学中文系学子在内的很多人都对他不了解,朱词的词学价值、词史地位都值得重新认识和发掘。二是市面上有关朱敦儒的专著,要么是繁体字,要么是竖排本,注释也多倾向学术性,不能满足更广范围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蒙发出自己写本朱词赏析性的书,以帮助更多读者对朱词的阅读理解。
收藏周刊:历经千载,我们今天应如何认识、评估朱敦儒先生其人,以及朱词的文学和文化史地位?
朱悦进:对此话题见仁见智,我的观点只是一己之见。总体上讲,朱敦儒在词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他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樵歌体”“希真体”。两宋词坛,群芳竞秀,但公认自成一宗、独自成体者寥若晨星。《全宋词》辑录词家1330余人,但公推为“体”的仅十位左右。二是他创制了最早的词韵《应制词韵十六条》,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对词韵学研究起到奠基作用。朱敦儒自身精通音律,也自创一些词牌。三是大大拓展了词风、词格和词的范式,朱敦儒词章展现出的深厚内涵和风格上的丰富多元在词史上确乎少见。尤其是他那充满渔樵之乐和山家风味的隐逸词,令其词章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风采,任何词家都无法取代。他不仅冲破了以往词的婉约、淫靡、晦涩之约束,提升了词的品格品味,而且以丰富的创作实践,为词艺拓展出更广阔生存空间,引入更具生命力的新范式、新境界。
收藏周刊:有评论说,“他在苏轼和辛弃疾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朱悦进:类似看法其实宋时就已有提出。如宋末诗人汪莘说:“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然流于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这个“三变说”揭示出苏、朱、辛三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实,朱敦儒词“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学界公认苏轼、辛弃疾为宋词豪放派之主帅,但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在北宋时并不具统领地位,“以诗为词”的东坡范式也未如后世那么受欢迎。连有“苏门六子”之称的陈师道都称:“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甚至批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这表明,在北宋文坛,苏词至少是颇受争议的。加之苏轼作品在北宋时一直遭禁,直到南宋高宗朝才解禁,因此,真正习摹苏词者并不多。
朱敦儒与苏轼性情相仿,都视陶渊明为“偶像”。陶渊明放达淡泊的胸怀、高标远韵的人格魅力和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构筑起苏、朱二人共同的精神追求。朱敦儒的一些词,明显带有习仿苏词的痕迹。尤其是其“清”“旷”色彩,正是效法苏轼,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学者认为:“苏轼‘以诗为词’之词学观的第一个真正继承者即是朱敦儒。”(郁玉英《朱敦儒词的阐释与接受》)正是朱敦儒对苏轼词的承继及创作实践,推动了“豪放派”词风的发展,并奠定其在词史上的流派地位。当然,这只是朱词对词史贡献的一个方面。
收藏周刊:从西京诗酒风流梦,到靖康之变后“南走炎荒”,您如何看待先生以词写史?
朱悦进:朱敦儒生活于两宋之交,此时期词作者多被称为“南渡词人群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清照和朱敦儒。北宋灭亡后,李从山东南奔至临安,就主要流寓于两浙。而朱敦儒则从中原到江南,再翻越五岭至南海,地理跨越度极大,他的词集中有二十多首是吟咏南粤生活。李清照的词大多抒闺怨之情,是记载个体命运变迁的小场景。而朱敦儒则可说是时代的记录者、吟咏者。同时,他的词又有着很强自传性。在他笔下,既有洛阳的金谷铜驼、吴地的蓬帆软语,也有南宋都城临安的歌妓采荷女,还有两广异域的“蛮溪鬼峒”、荔青桄榔。从中原到岭南再北归临安,万里风尘云烟,一路世俗民情,都在其词中呈现。民间的“烧灯”“踏青”“斗草”风俗,他一一录下;士人的雅集盛会乃至宫中的“御雪宴”,也不曾遗漏。阅读其词章,好似读两宋社会史。在宋代词坛,能以词章全面呈现时代风云变迁者,只有辛弃疾可与其比肩,但辛弃疾与朱敦儒不是同时代人。应该说,纪实叙事性表达,是朱词的很重要特征。中华文化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词赋的文学性易于被更多人所接受,朱敦儒“以词写史”,对中华文化和历史传承的贡献很大。
收藏周刊:您能否从题材、意境等方面,为我们讲述一下朱敦儒先生的“创新”精神?
朱悦进:借用胡适的一段话:“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确实,朱敦儒的词,无论题材,还是意境、表现方式都有许多独创性。
他打破了“花间词”的娱宾遣兴、绮罗香泽之窠臼,把词的触角伸向现实生活,构筑起词体的抒情言志功能。其词章的清奇逸趣以及无所禁忌、包罗万象的纪实叙事性表达,更为词体范式的发展提供新摹本。他又是山水画高手,在词的创作上常用写意的手法,令词章极具诗情画意,让人赏心悦目。
总之,朱敦儒大大拓展了词风、词路,口语式的议论、散文化的表述、天上人间的浪漫玄想转换以及珠玉般跃动闪耀的佛机禅理等等,都令词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呈现方式更为立体多元。
收藏周刊:作为先生的“隔世知音”和研究评注者,这些年,您从先生身上获得了怎样的精神力量?
朱悦进:不敢说“隔世知音”,只能说是朱词的学习研究者。在研读朱词过程中,我认为最大收获有两点,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独立精神。
朱敦儒可说是两宋之交最具士人风骨的词人。他出身仕宦之家,家境优渥。北宋时,他诗酒风流、纵情山水,是完全不谙世事的“词仙”,当外敌入侵,故土沦丧,他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这也促使其成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无论南奔途中,还是在南粤两广,他心心念念匡复故土,回归中原。其词作,家事与国事总融为一体,放在整个南渡爱国词人群体中,他的家国情怀都表现得最为真挚和深厚。
两宋之交是个特殊历史时期,外侮内患、民族危亡,人性、道统伦理等都在动荡时局中挣扎。这也导致士人的自尊心、自主性受到挑战。朱敦儒正是在人性丧失、道德沉沦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寻找、追回失落了的自我。他虽说狂放不羁,但本性清高孤傲,始终追求个体心灵的自由独立。他不附炎趋势,不随波逐流,“进则尽节,退则乐天”。他总把个性精神寄托于梅、菊等吟咏对象中。他的人生态度是审美的,也是诗化的,同时,他又很理性自律,词章常蕴含内省和反思精神,这一点无疑也值得现代人学习。
收藏周刊:本书为朱敦儒家族史研究提供了何种重要信息?
朱悦进:本书对朱敦儒的家族和家庭均披露了一些此前公开出版物从未见载过的信息。首先是对朱敦儒的家族起源等做了首次披露;其次是提供了其夫人及子女情况。朱词中有几首涉及悼亡的词,但其夫人姓甚名谁无人知晓,本书根据家谱和相关历史文献相互印证,首次确认其夫人叫钱端回。再次是提供了朱敦儒与抗金名将宗泽的关系,两人为儿女亲家。 这些史料过去从未公开。
收藏周刊:作为评注者,在为经典书写赏鉴文字时,应如何把握专业和通俗的边界?
朱悦进:专业与通俗并非截然对立的概念,也无明确界线。专业的可以很通俗,通俗的也可呈现出专业。当然,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在对古诗词作解读时,可有相对专业和通俗的分工。比如,对普通读者,注释、赏析应尽量详细、浅显易懂,而对专业人士,则可提供相对简练、精深的资料或提示。《朱敦儒词赏鉴》的目标读者定位于大众读者,在写书时,考虑到阅读需求,注释尽量详尽,赏析也尽可能通俗易懂,但能否得到认可,还有待读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