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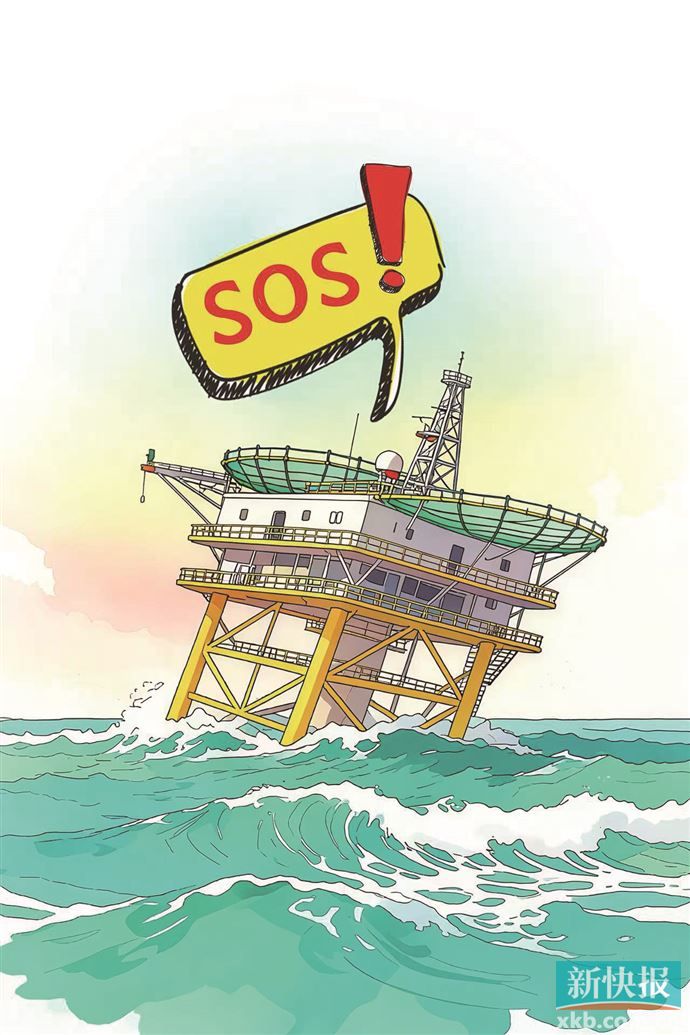
广东高院发布一批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海上作业平台、海洋养殖平台是否算“船舶”?邮轮“包切舱”模式是否合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海事审判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涉及海上风机作业平台性质及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的认定、海洋养殖平台的法律属性界定等难点和热点问题。
据悉,2024年至今年8月,广东法院共审结一审海事海商案件4317件,充分体现了广东法院以高质量海事审判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依法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服务海洋产业、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司法新实践。
各执一词
●海上作业平台界定引发争议
●法院认定属船舶维持原裁定
“升某”平台是总吨6700的自升式海上风机作业平台。它的《船舶国籍证书》上写明的船舶类型是“水上平台”,并且通过了中国船级社的检验,取得了相关证书,被登记在船舶名录中。
这个平台在一次海上风电场进行插桩作业过程中,因为桩腿穿刺船体而导致沉没。当地海事局认定,这是一起由“升某”平台自身原因引起的单船责任事故。
事故后,“升某”平台的承租人——某海洋工程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目的是对该事故可能造成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责任设定限制。
但某财产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升某”平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所定义的“船舶”,因此该海洋工程公司没有权利申请赔偿责任限制,要求法院驳回其设立基金的申请。
结果: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升某”平台有船籍,从平台证书及其功能看,其为用于海上风机安装、维护的自升式平台;从其本身物理性能看,平台虽无动力,但能漂浮在海上,通过拖船拖带可在海上航行及在不同地点进行移动作业。
虽然平台在作业时需用桩腿固定在海床上并升离至水面之上,但这是由于其作为海上风机作业平台的特定功能所决定的,不足以影响其作为“海上移动式装置”的属性。“升某”平台可认定其为“海上移动式装置”,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的“船舶”。
“升某”平台在作业过程中沉没可能导致的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请求,属限制性债权,某海洋工程公司有权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遂裁定准许某海洋工程公司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某财产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海上风电项目是海洋新业态和海洋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产业之一。海上风机作业平台作为建设海上风电的重要设施,在海上作业时面临风浪及复杂海洋地质条件等风险。本案将海上风机作业平台准确界定为“海上移动式装置”,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所规定的“船舶”,确认承租人或经营人基于该平台产生的海事赔偿请求享有责任限制权利,有利于保障风电企业生产经营,护航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海上救助
●海洋养殖平台遇事故
●救助费用迟迟未付清
横某公司有一艘名叫“某洲号”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在从大连拖往珠海的途中发生了事故。
事后,横某公司找到正某公司,先后签了好几份合同,包含救助合同、拖带协议、安装工程合同,委托正某公司对“某洲号”进行救助、拖带进港,并在指定海域定位安装网箱作业。
正某公司按约定完成所有作业后,横某公司却没有付清相关费用。
于是正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横某公司及其唯一股东北京中某公司连带支付相应费用及违约金。
结果: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结合“某洲号”养殖平台的特点,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船舶”,但其为非永久和非有意地依附于岸线的财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财产”。
横某公司未依约支付救助费、应急拖带费、安装费,构成违约,北京中某公司未证明横某公司财产独立于北京中某公司的财产,两公司应连带支付救助费、应急拖带费、安装费及违约金。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随着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涉及海洋养殖平台的纠纷逐渐增多。对于各类型海洋养殖平台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的“船舶”,实务中存在一定争议。人民法院结合海洋养殖平台的具体特点,依法界定本案海洋养殖平台的法律属性,进而认定对该平台实施的救助属于海上救助,健全深远海数字化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相关法律规则体系,助力广东全链条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取得新突破。
分而售之
●确认“包切舱”模式合法性
●法院判违约方付差额费用
有一家外国公司负责运营“云某”号邮轮,它把整艘邮轮的船票以“包切舱”的形式向云某旅行社销售。云某旅行社买下这些船票后,再自己对外销售。
之后,云某旅行社和明某深圳分公司签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云某旅行社向明某深圳分公司提供这艘邮轮5天4晚自深圳蛇口至香港某航次的1674间舱房;而明某深圳分公司则需要支付相应的舱房费用。
合同中还明确,明某深圳分公司承诺:该航次的实际乘船人数不能低于3900人,并且旅客在船上的额外消费总额不能低于696万港元。如果达不到这两个标准,明某深圳分公司就需要按约定补付一笔钱,包括客房服务费、港务费以及船票款差额等。
之后,邮轮如期完成约定航程,云某旅行社以实际登船人数和在船消费总额都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明某深圳分公司支付上述各项差额费用。
结果: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云某旅行社持有出境游业务经营许可,其将从境外邮轮经营者处取得的对特定邮轮舱位的使用权有偿转让给明某深圳分公司,明某深圳分公司再将特定邮轮舱位单独或作为旅游产品之组成部分向旅游者销售,两公司分别通过相关合同的差价获得盈利。
案涉舱房供应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航次实际登船旅客人数低于双方约定,明某深圳分公司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旅客船上付费项目消费总额未达到约定最低标准,遂判决明某深圳分公司向云某旅行社支付部分客房服务费差额、港务费、船票补偿款等,其总公司明某旅游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鉴于明某深圳分公司于二审期间注销,故改判明某旅游公司向云某旅行社支付上述费用。
典型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香港、深圳、广州等邮轮母港排名居全国前列,邮轮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本案对外国邮轮公司与持有出境游业务经营许可的国内旅行社在“包切舱”模式下对外订立舱房供应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涉外邮轮旅游行业,支持邮轮旅游行业创新业务合作模式、开辟邮轮经济新赛道,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洋旅游高端产业高质量发展。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全小晴 王美玲 胡君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