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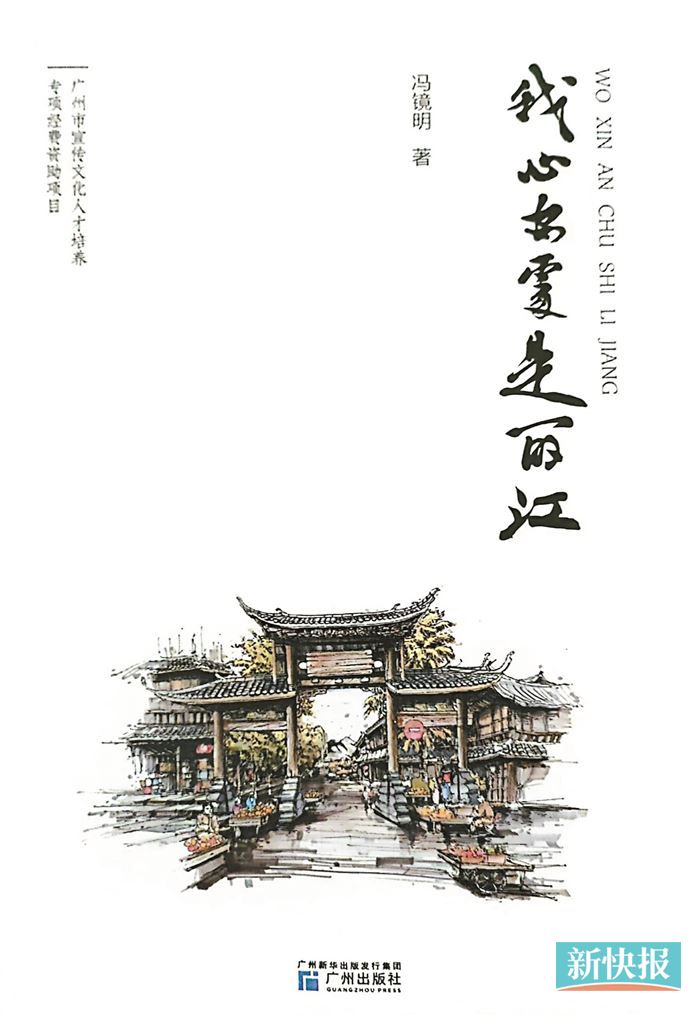

■文化学者 冯达榳
《我心安处是丽江》这个书名取自苏轼的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冯镜明先生(笔名“马修”)与丽江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通过七次探访和数十年的思考,冯镜明先生在丽江找到了心灵的安顿之所,并通过精湛的文字将这种体验传达给读者。
当我们谈论丽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四方街的喧嚣繁华,是玉龙雪山的巍峨壮丽,还是小桥流水的恬静诗意?在《我心安处是丽江》中,我看到了一个超越寻常旅游叙事的丽江,一个承载着历史厚重、人文温度与生命思考的丽江。
不止于记录:
媒体人的执着与深情
作为资深媒体人,作者对丽江的书写并非偶然的灵感触发,而是长达数十年的执着追寻。从1996年丽江大地震后作为特遣记者第一时间抵达灾区,到后来多次奔赴丽江进行回访和采风,他七赴丽江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坚守与热爱的故事——一位新闻人执着行走,在丽江的柔软时光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与那些浮光掠影的旅行作家不同,作者对丽江的探索带着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敏锐和作家的深沉思考。他的老朋友评价他“并非副刊记者,却对写作和文学有一种执着的关注和热情”。这种对文字的热忱在《我心安处是丽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文字“娴熟精准、徐疾有致地书写着他对丽江的历史、文化、人和物的热爱”。
历史与现实交织:
古城的多维画卷
《我心安处是丽江》在结构上分为两辑,第一辑10篇文章,第二辑27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丽江的多维面貌。冯镜明先生不仅关注丽江的当下,更追溯其悠久的历史脉络。他追随忽必烈、徐霞客的脚步,参照美籍奥地利人洛克和俄国人顾彼得的指引,深入了解并写下了那些不为人知的史迹与传说。
书中对纳西古乐的宣科和泸沽湖之恋里的大狼等人物的描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故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摩梭男女的随情至性,呈现了“万物归元,天地合一”的生活哲学。
灾难与重生:
从地震到文化坚守
作者第一次到丽江是在1996年大地震之后,这种始于灾难的相遇赋予了他的丽江书写特殊深度。他不仅看到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更感受到了丽江人坚强不屈的抗灾精神。
这种从灾难到重生的叙述线索,使《我心安处是丽江》不仅仅是对一个古城的赞美,更是对生命韧性和文化传承的致敬。冯镜明先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向我们展示了丽江如何从灾难中重生,如何保持其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又拥抱时代的变化。
文学精神的归宿:
为什么是丽江?
在众多城市中,为什么作者独独对丽江情有独钟?或许是因为“丽江的静水深流,是每一个心怀文学梦想的人的一个归宿”。丽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方宁静,让心灵得到栖息和滋养。
作者自己也曾说过,他要写一本关于丽江的书,因为对于丽江,他有“不一样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源于丽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更源于丽江所能提供的精神上的安顿和心灵上的共鸣。
书写的意义:
坚守文字价值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的文化人也变得“懒语”了:“能不说的话,尽量不说;能用嘴说的,就不动笔。”人们对“书写”在当下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动摇:既然人生都是虚妄的,用文字去记录个体存在的痕迹,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作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应了这种困惑。他曾表示:“唯有文字,庄严地宣告生命曾经存在。”这种对书写意义的坚守,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游记范畴,成为一种生命存在的证明。
作者对丽江的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于友人感叹:“黑龙潭水深千尺,不及马修丽江情。”他对书写意义的坚守,他对文字价值的确信,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其洋溢在全书中的真情实感。它本身就是一个宣言: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真诚的文字永远拥有打动人的力量。
超越旅游攻略:
深入灵魂的丽江书写
《我心安处是丽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指南或景点介绍。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超越了实用性的旅游指南,提供了更加深刻的关于生活、文化、历史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它邀请读者不是简单地去丽江旅游,而是像作者一样,用心去感受丽江,理解丽江,从而在灵魂的江湖中照见自己。
这本书不仅是对一座古城的深情告白,也是对生活意义的深刻探索。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归宿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能够让我们心灵安顿的状态。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只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探索精神,就能找到自己的“丽江”。
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我心安处是丽江》这样的书籍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慢下来,用心去感受一个地方,深度体验一种文化,真诚地记录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这或许就是冯镜明先生和他的丽江之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